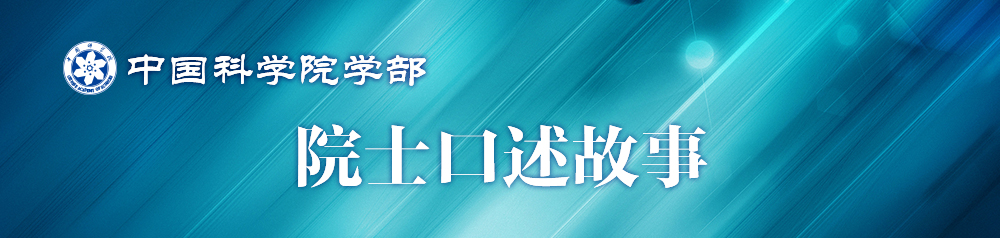郑儒永:回忆邓叔群先生在微生物研究所真菌室的日子

1957年,邓叔群在南京郊外采集真菌标本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我于1953年自广州华南农业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真菌植病研究室工作,导师是戴芳澜先生。1956年真菌植病研究室扩大成为应用真菌学研究所,1958年底与北京微生物研究室合并成为微生物研究所至今。
早在学校时,我已知道戴芳澜先生和邓叔群先生是我国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参加工作后又从戴先生处得知邓先生还是我国森林学和森林病理学的先驱。直到1955年邓先生从沈阳农学院重归中国科学院,参加真菌植病研究室的工作我才第一次见到了邓先生本人。
邓先生回院后,除担任真菌植病室副主任和应用真菌学所及微生物所副所长外还兼任真菌组组长(1956年前)和真菌室室主任(1956年后),我则在1955年到1966年间一直是真菌组或真菌室的业务秘书,与邓先生有许多工作上的接触和联系,亲眼目睹了邓先生是如何献身科学忘我工作以及如何心怀壮志为加速我国真菌学事业的发展而努力奋斗的。这些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有些事情的具体时间和细节亦已在记忆中逐渐淡去,但邓先生对国家和真菌学所作的贡献,他的奉献精神,他对我们大家的帮助和影响则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为了发展真菌学,邓先生是从两头抓起的。一头是基础资料的累积,具体做法是制定周密的采集、调查计划和组织大家分工合作鉴定标本,写出中国真菌志(当时邓先生称作真菌专志);一头是真菌资源的研究,即害菌的防治和益菌的利用,具体做法是密切配合社会上的需要,为生产单位排忧解难,提供所需的真菌,或是为生产上已经在使用的真菌鉴定学名并提供有关信息,遇有生产单位不能解决的技术问题则设题研究。前者为长远打下基础,后者服务于当前的需要。
在邓先生来所并主持真菌室工作以前,室内各组各自制定出差计划分散采集标本,研究人员不能较长时间地逗留在野外,致使本来就不多的差旅经费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邓先生招收了十名标本采集员,亲自为他们讲课介绍真菌的基础知识,亲自带领他们到京郊的山区考察各种真菌,示范如何采集标本、如何作采集记录和采后处理等等。同时,邓先生认真地查阅了地图集并向地理研究所的同志了解相关信息,初步选出了十个覆盖全国的有代表性的山系作为长远驻守采集的对象。遗憾的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宏伟设想未能实现。尽管如此,邓先生仍然抓紧一切机会组织多次到全国各重要地区的采集并采回大批的标本,为以后开展全国真菌志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对真菌学科的整体发展,邓先生也倾注了不少心血。邓先生是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学部委员(院士)和政协委员,每次从院部或政协会议开会回来,他都会非常兴奋地把会上了解到的政府对科技界在建设新中国方面的要求传达给大家,要求每一个人都落实到与真菌学有关的工作中去,他常常感叹真菌事业的基础太薄弱,人才也太缺乏。为此,他一次一次地制定修改规划,加快人才培养、扩大队伍,加快计划的实施,加快研究的进展,早出成果,好为国家多作贡献。在邓先生热情洋溢的鼓舞下,在他详细尽心的安排下,尤其是在他以身作则的带动下,当时的真菌室上下一心,大多数人都努力工作,无论是出成果还是出人才,都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为了响应号召向党中央献礼,大家决定将历年所采标本中没有人设题研究,因而大量积压在标本室中落满灰尘的上百大捆寄生真菌标本和大堆的盒装大型真菌标本突击进行初步鉴定到属以便入柜保存。由于研究寄生真菌的人较多,经过奋战,勉强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了任务;大型真菌方面,只有邓先生自己和他所领导的研究组作这方面的研究,而他的研究组还有别的献礼任务,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几百号大型真菌标本的突击鉴定任务就落到了邓先生一个人的肩上。邓先生二话不说,立即行动,连续奋战多天,最后一连三天日以继夜地把最后的标本全部鉴定出来了。邓先生鉴定的标本,和我们大家只按原定指标鉴定到属不同,他是超指标鉴定到种的,而且保持了正常情况下的规格,在鉴定签上工工整整地一笔一划把菌的属名、种名、定名人写得一清二楚。此外,邓先生还提出了要以最快的速度研究出十种食用真菌和药用真菌的人工栽培方法,研究出通过中间生产鉴定的真菌发酵造纸工艺,结果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全部完成了。邓先生除大跃进年代事事带头,在正常年代的日常工作中也同样事事带头,他每天很早来到实验室,常常是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他的工作时间总是比别人长,工作成果也总是比别人显著,他鉴定的标本比任何人都多,可惜最后几年根据标本研究整理写成的巨著书稿《蘑菇谱》(约40万字和600幅彩图)以及另外一些重要论著的稿件在十年动乱中丢失了。邓先生的得力助手是他的女儿邓庄,邓先生的许多工作设想,特别是在真菌的应用研究方面,都是通过指导邓庄,由她带领其他人员实际完成的;另外,邓庄还有很好的绘画天赋,邓先生著作中的真菌线条图或彩图大多数也是由她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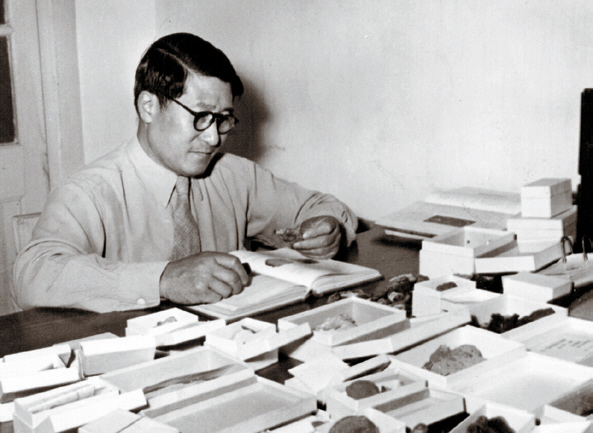
1956年4月,邓叔群在进行中国多孔菌分类研究工作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对真菌室的日常管理工作,邓先生同样尽心尽责。每年的工作计划邓先生都要亲自布置到课题组去,课题组交上计划后,他亲自审查,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再返回课题组去;年中、年末两次根据存底的计划副本一一检查执行情况,计划完成得不好的课题组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邓先生就会严肃地在全室会议上批评组长,不管组长的资格老不老。那个时期的经费很少,和现在不同,不是由课题组自由申请和自由使用,而是由各个课题组在年初提出计划,集中到研究室后由研究室主任审批后上报到所里,所里集中上报到院里,院里拨款然后一步一步返回来。为了争取到多一些经费,有的课题组会把预算订得高一些,但邓先生严格把关,审查时很难通过。他总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节约的原则来制定全室的预算,因此,真菌室上报到所里的经费预算往往是全所最低的,久而久之,在所中甚至造成了真菌室不花钱也能工作的错觉。不过,由于分类工作的特殊性,戴、邓先生都十分重视图书、期刊的加强和补充,在所学术委员会等讨论图书、期刊的订购计划时,他们都会为与真菌有关的图书、期刊争取到必要的种类,因为真菌室对待经费预算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尽人皆知的。对真菌室的培干工作,邓先生也很在意。尽管那时中国科学院实行导师责任制,年青的科研人员都由各自的导师负责培养,邓先生仍然为大家组织了全室的读书报告会,亲自为大家讲演并参加年青人的报告会,听后积极发言参加讨论和指出不足之处。邓先生还多次组织全室性野外采集,在采集过程中,邓先生不厌其烦地为大家讲解各种真菌的生态习性、形态特征、分类地位、采集时应注意的事项等等,由于邓先生有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和渊博的学识,跟随他出去一天,学到的东西是很多的,更重要的是加深了书本上的知识和培养了对真菌工作的兴趣。北京潭柘寺是一个有相对多的真菌可采的地方,每年研究室来了新成员,邓先生就会带领前去一次,目的是为了培养年轻人而并非为了自己工作所需。
在过去的年代里口号很多,其中有一个口号是邓先生很欣赏的,那就是“实干、苦干加巧干”,这实际上也是邓先生自己工作作风的最好写照。邓先生的实干,表现在不放空炮,说到做到;苦干表现在一干到底,分秒必争;巧干则主要表现在工作的计划性以及方法的准确性。由于每做一件事,邓先生事先都有周密的考虑和安排,做什么、怎样做一清二楚,做起来就不费劲,因此,邓先生忙而不乱,同时做几件事不会互相影响,总能高质量、高效地按时完成。
邓先生不光是一个实干家,也是一个改革家。前面提到的一些事情,如对标本采集、标本室管理等,已足以说明他思想活跃而不因循守旧。甚至对一些政策性的东西,邓先生也敢于提出改革性的不同看法。例如,早年中国科学院所属各所都执行导师责任制,大学毕业生到研究所后分配到固定的导师下面工作。邓先生提出,这样无异于封建婚姻,导师、学生双方都没有彼此选择的权利,如果一个不好的学生分配给一个好的导师,对导师来说是杀鸡用牛刀,还要负不能把他培养成材的责任;反之,一个好的学生分配给一个不够好的导师,学生得不到最好的培养,结果是延误了学生成材的时间。因此,邓先生主张导师和学生应该有彼此相互选择的机会。其实这正是现在研究生和指导老师的关系,研究生报考时可以选择导师,导师也可以择优录取学生。不过,当时是全院性的规定,在一个研究所进行改革谈何容易。另一个例子是邓先生对论资排辈的许多做法一向非常反感,在提级提职、分配仪器经费等工作中总想摆脱论资排辈的框框而按实际工作表现来处理,实际上这也是今天在改革中的做法,如课题组长、行政职务的竞争上岗等,但在当时的大气候下是行不通的。在我担任研究室业务秘书期间,邓先生的这种改革精神处处可以体会得到。
邓叔群先生在本可大展宏图的年龄过早逝世,是我们国家的重大损失,更是全世界、全中国真菌学界、森林学界以及植物、森林病理学界的重大损失。邓先生的大半辈子生活在一个艰苦的时代,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而成材并作出巨大贡献。解放后工作条件虽有所改善,但不幸遭遇十年动乱,许多尚未完成的工作付诸东流,实在是叫人痛心。现在社会安定,国家富强,科教工作比任何时候都受到重视。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作为邓先生的晚辈和学生的我们每一个人,更应该以邓先生的严谨治学、实干巧干精神为榜样,激励我们为国家的富强昌盛作出更大的贡献。
(节选自《菌物系统》.2002,(04):468-472)